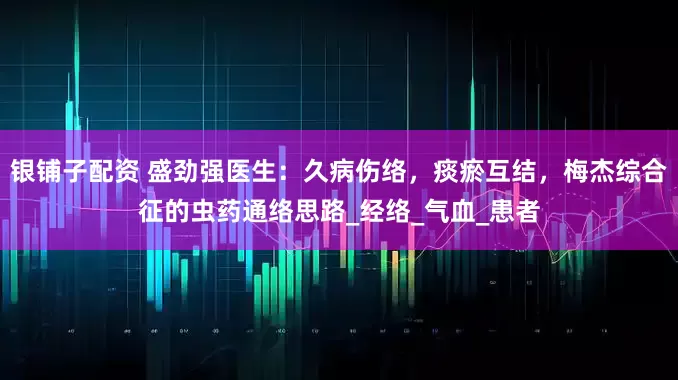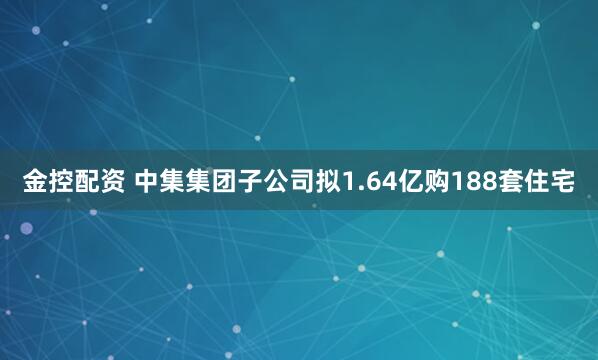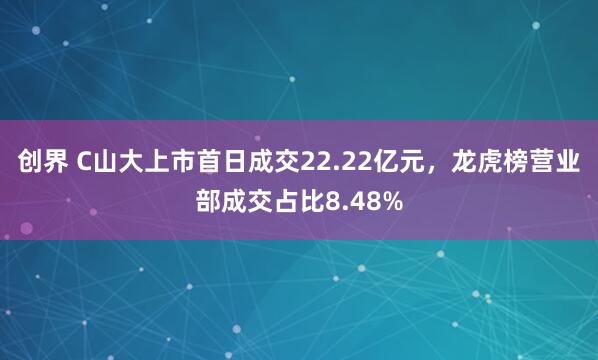在进战犯管理所之前新影宝,杜聿明算王耀武的半个长官,进了战犯管理所之后,王耀武又成了杜聿明的半个领导,也算是历史跟这两个中将司令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王耀武担任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的时候,杜聿明先后出任东北保安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就在杜聿明辽沈淮海两头跑的时候,王耀武被俘了,在王耀武被俘前,杜聿明还到济南“视察”过。
王耀武在《济南战役的回忆》(发布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中回忆:“南京统帅部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黄伯韬、邱清泉、李弥三个兵团与陈毅部的主力作战,以解济南之围。我认为解放军的作战力量已大为增长,固守济南必须调整编七十四师或整编八十三师来增防,否则没有把握。杜聿明的意见与我相反,他说:‘只要加强工事,不增加兵力,济南也可以固守。如守不住,即使再增加部队,也守不住。因此,我不同意再增加部队。如若打起来,只要你们能守十五天,我指挥的部队一定可以到达济南,解你们的围。’”

杜聿明虽然不是王耀武的直接长官,但他能调动好几个兵团,而王耀武的第二绥靖区是与兵团平级的(徐州“剿总”有些兵团前身就是绥靖区),我们甚至可以说杜聿明当时的态度,也能间接决定王耀武的命运。
王耀武的参谋长罗幸理因为支持王耀武的意见,请求杜聿明向济南增兵,并表示如果不增兵,济南三五天就得完蛋,杜聿明很不满意地向老蒋告了一状,这件事王耀武也写了:“杜对罗所说的话很不满意,他回到南京见蒋介石时曾向蒋报告,说罗幸理没有固守济南的决心,身为参谋长,不但不设法鼓励士气,反而尽说泄气的话,思想有问题。蒋也未作处理。”
风水轮流转,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王耀武成了学习委员,地位就在“缝纫组组长”杜聿明之上了,沈醉的《战犯改造所见闻》中生动地描绘了王耀武“视察”的奇妙场景:“在管理所下面除了十多个学习小组和以后增设的劳动小组外,还有一个由战犯自己推选出来的主管学习生活等的委员会,主管学习的委员是王耀武,宋希濂是文娱委员,庞镜塘生活委员,曾扩情是卫生委员。这四位同学来缝纫组检查,他们看了一下便问我们对学习、生活、文娱、卫生等有什么意见。杜聿明照例回答:‘都很好,没意见。’”

战犯们在管理所被称为学员,学员之间互称同学,但同学和同学的地位却不一样,如果把功德林比作一所大学,那么王耀武就是学生会干部,而杜聿明也就是寝室长,王耀武检查缝纫组新影宝,跟学生会查寝差不多。
沈醉那句“杜聿明照例回答”,说明王耀武到各组检查是日常工作,就连各小组学习情况,也要上报给王耀武,这一点沈醉也写得很清楚:“学习小组长之上还有一个学习委员,直接由管理所负责人领导,王耀武就是学习委员。每次学习完,各学习小组便向他汇报各组学习的情况,由他汇总向管理所汇报,管理所有什么事也由他向各小组去传达。”
王耀武对杜聿明并没有任何“打击报复”,而且相处得还比较融洽,看到这里可能就有读者要发问了:既然王耀武丢失济南、战败被俘跟杜聿明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王耀武为啥不恨杜聿明?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肯定王耀武的人品——王耀武的人品,沈醉也是极为佩服的:“他的确是认真负责如实地反映问题,不仅得到领导上的信任,也得到所有的“同学”的信任。”

王耀武作为学习改造积极分子,是不可能对前期相对落后的杜聿明进行任何打击报复的,而且他也十分清楚:杜聿明在援助济南的时候确实出现了战略误判,但主要责任并不在他,而在老蒋和邱清泉、李弥。
1948年9月14,王耀武亲自飞到南京向老蒋求援,请求把自己带过的整编七十四师空运到济南,老蒋只是“嗯”了几声,没说行也没说不行,王耀武也没敢再问。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整编七十四师就是原来的七十四军新影宝,王耀武当了很长时间七十四军军长,1947年5月七十四师在孟良崮被歼灭的是主力,还有一千多人没上战场(伤兵)或逃了出来,就在这一千多人的基础上又重建了整编七十四师,而且依然是美械装备。
老蒋最后只给王耀武空运过去整编七十四师五十八旅一七二团七个连,这七个连差点成为王耀武的救命稻草,王耀武回忆:“一七二团团长为了守住邮政大楼,在解放军猛烈火力射击下,把领事馆的部队强行撤至邮政大楼内。在冲过马路时,他们被打死打伤很多,死尸横卧在马路者到处皆是。该大楼虽被层层包围,守军仍负隅顽抗,战斗仍甚激烈。守军利用大小射击口向解放军猛烈射击,并由门窗向外投掷手榴弹,但转瞬间就被解放军打死或打伤在射击口边上或横卧在窗上;这样不断地被打死,守军不断地将死尸拉开或推下楼去,继续作战。”

王耀武负隅顽抗,就盼着杜聿明的援军及早到来,但杜聿明那里又出了新状况,王耀武也知道杜聿明是咋想的:“杜本想待围攻济南的解放军受到重大的伤亡而攻击顿挫之后,再解济南之围。因此,他本来打算在济南战事开始后的第五天,才令增援部队出动。”
不管怎么说,杜聿明还是派了邱清泉兵团、黄百韬兵团和李弥兵团,前去救援,结果邱清泉从商丘、砀山出发,走到城武、曹县一带就不走了,黄百韬和李弥两个兵团一直借口没有完成集结而迟迟不动。
王耀武从济南被围之初就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他之所以迟迟没跑,是因为他被刘峙忽悠了——1948年9月23日上午9时,刘峙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到济南上空,用无线电话与给王耀武打气,并表示“援军进展很快,几天就可以到济南”。
按王耀武的算计,邱清泉李弥就是爬,再过两三天也该到济南外围的,他没想到邱清泉等人根本就没往济南爬,遭遇阻击后迅速后撤脱离,根本就没想死打硬冲。

黄百韬后来被包围在碾庄圩的时候抱怨友军不救,却忘了早些时候张灵甫和王耀武也曾经眼巴巴等着他救援,结果都是一样干等不来、全军覆没。
邱清泉虽然是杜聿明的“老部下”,但自从他当上第二兵团司令后,也不太听杜聿明的话了——当年的蒋军将领,都是以保存实力为第一要务,消耗自己的部队去救别人,十个司令里得有九个不干,去的那个也是磨磨蹭蹭。
王耀武守济南,失败是必然的:老蒋口惠而实不至,杜聿明判断失误,邱清泉、李弥、黄百韬迁延不进,内缺粮弹外无救兵的王耀武只能跑路。
尽管王耀武早有逃跑预案,但最后还是没能逃出天罗地网,等杜聿明和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等人被俘后送到“解放军官教导团”的时候,王耀武已经站在大门口准备迎接了——文强在《口述自传》和《新生之路》中都描述了那有趣的场景,这里就不再复述了。

王耀武和杜聿明、文强都来都进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文强先去的),不管是在山东还是在北京,王耀武表现得都很积极,他是看明白了:自己被老蒋忽悠到山东当省政府主席和第二绥靖区司令,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早点解甲归田,开着那两台美式拖拉机回老家种地。
王耀武说他谁都不恨,只恨老蒋——他在抗战胜利后就躲进了医院:“既然功成名就,不如激流勇退,既可以以抗日名将的身份流芳百世,也可同家人团聚,尽享天伦之乐。如涉入内战,恐将身名两难全。”
老蒋赶鸭子上架,王耀武抹不开面子,这才有了济南之败,所以“明白人”王耀武是不恨杜聿明的:杜聿明指挥不动邱清泉李弥,自己也指挥不动李仙洲,因为他们上面还有老蒋、陈诚、顾祝同、刘峙,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有老蒋的瞎指挥,杜聿明就是拼了老命,能救出王耀武吗?王耀武比其他被俘将领更明白这一点,您说他能恨杜聿明吗?
兴盛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